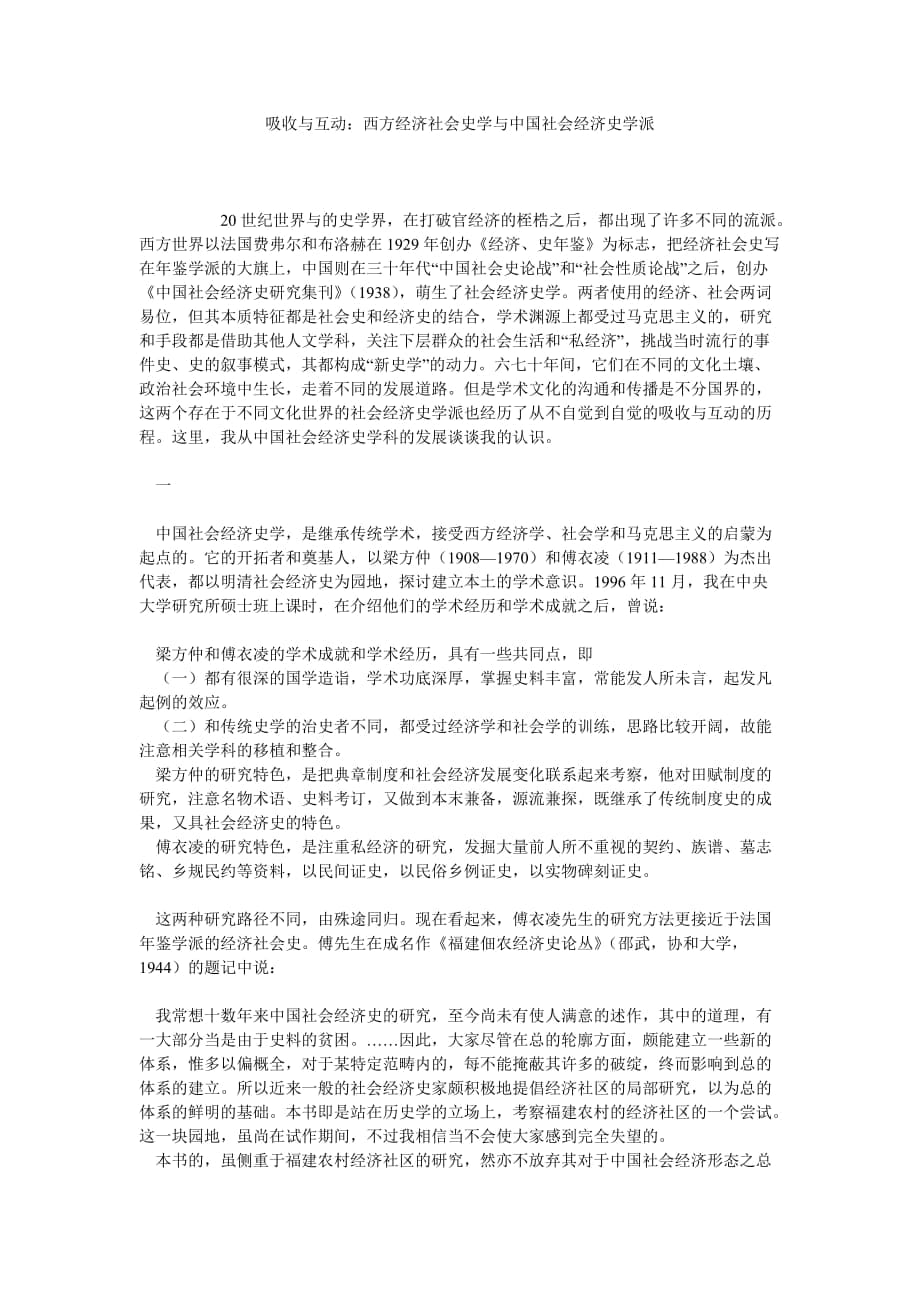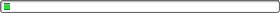《吸收與互動(dòng):西方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學(xué)與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》由會(huì)員分享���,可在線閱讀���,更多相關(guān)《吸收與互動(dòng):西方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學(xué)與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(2頁珍藏版)》請?jiān)谘b配圖網(wǎng)上搜索��。
1�����、
吸收與互動(dòng):西方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學(xué)與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
20世紀(jì)世界與的史學(xué)界��,在打破官經(jīng)濟(jì)的桎梏之后�,都出現(xiàn)了許多不同的流派�����。西方世界以法國費(fèi)弗爾和布洛赫在1929年創(chuàng)辦《經(jīng)濟(jì)���、史年鑒》為標(biāo)志��,把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寫在年鑒學(xué)派的大旗上�,中國則在三十年代“中國社會(huì)史論戰(zhàn)”和“社會(huì)性質(zhì)論戰(zhàn)”之后���,創(chuàng)辦《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研究集刊》(1938)���,萌生了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。兩者使用的經(jīng)濟(jì)���、社會(huì)兩詞易位,但其本質(zhì)特征都是社會(huì)史和經(jīng)濟(jì)史的結(jié)合�����,學(xué)術(shù)淵源上都受過馬克思主義的���,研究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學(xué)科�,關(guān)注下層群眾的社會(huì)生活和“私經(jīng)濟(jì)”�����,挑戰(zhàn)當(dāng)時(shí)流行的事件史�、史的敘事模式����,
2、其都構(gòu)成“新史學(xué)”的動(dòng)力�。六七十年間,它們在不同的文化土壤、政治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中生長���,走著不同的發(fā)展道路�。但是學(xué)術(shù)文化的溝通和傳播是不分國界的�����,這兩個(gè)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也經(jīng)歷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吸收與互動(dòng)的歷程��。這里��,我從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談?wù)勎业恼J(rèn)識����。
一
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,是繼承傳統(tǒng)學(xué)術(shù)���,接受西方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���、社會(huì)學(xué)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為起點(diǎn)的。它的開拓者和奠基人���,以梁方仲(1908—1970)和傅衣凌(1911—1988)為杰出代表��,都以明清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為園地����,探討建立本土的學(xué)術(shù)意識。1996年11月����,我在中央大學(xué)研究所碩士班上課時(shí),在介紹他們的學(xué)術(shù)經(jīng)歷和學(xué)術(shù)成就之后
3�����、�,曾說:
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學(xué)術(shù)成就和學(xué)術(shù)經(jīng)歷,具有一些共同點(diǎn)�,即
(一)都有很深的國學(xué)造詣,學(xué)術(shù)功底深厚��,掌握史料豐富�,常能發(fā)人所未言,起發(fā)凡起例的效應(yīng)�。
(二)和傳統(tǒng)史學(xué)的治史者不同�,都受過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和社會(huì)學(xué)的訓(xùn)練,思路比較開闊�,故能注意相關(guān)學(xué)科的移植和整合���。
梁方仲的研究特色,是把典章制度和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變化聯(lián)系起來考察���,他對田賦制度的研究���,注意名物術(shù)語、史料考訂�,又做到本末兼?zhèn)洌戳骷嫣?���,既繼承了傳統(tǒng)制度史的成果,又具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的特色���。
傅衣凌的研究特色�����,是注重私經(jīng)濟(jì)的研究��,發(fā)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視的契約���、族譜�、墓志銘���、鄉(xiāng)規(guī)民約等資料���,以民間證史,以民俗鄉(xiāng)例證史��,以實(shí)物
4�、碑刻證史。
這兩種研究路徑不同���,由殊途同歸?,F(xiàn)在看起來�����,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國年鑒學(xué)派的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�。傅先生在成名作《福建佃農(nóng)經(jīng)濟(jì)史論叢》(邵武,協(xié)和大學(xué)�,1944)的題記中說:
我常想十?dāng)?shù)年來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的研究,至今尚未有使人滿意的述作��,其中的道理,有一大部分當(dāng)是由于史料的貧困����?!虼耍蠹冶M管在總的輪廓方面����,頗能建立一些新的體系,惟多以偏概全���,對于某特定范疇內(nèi)的����,每不能掩蔽其許多的破綻��,終而影響到總的體系的建立����。所以近來一般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家頗積極地提倡經(jīng)濟(jì)社區(qū)的局部研究,以為總的體系的鮮明的基礎(chǔ)��。本書即是站在歷史學(xué)的立場上����,考察福建農(nóng)村的經(jīng)濟(jì)社區(qū)的一個(gè)嘗試��。這一塊
5����、園地�,雖尚在試作期間,不過我相信當(dāng)不會(huì)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���。
本書的�,雖側(cè)重于福建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(jì)社區(qū)的研究���,然亦不放棄其對于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形態(tài)之總的輪廓的說明���,尤其是對于中國型封建主義特點(diǎn)的指明的責(zé)任。譬如中國封建社會(huì)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殘余物在中國封建社會(huì)史所發(fā)生的作用這一些問題���,從來論者都缺少具體的說明�����,故本書特搜集此項(xiàng)有關(guān)資料頗多……其中所論�,雖不敢說有什么創(chuàng)見,但為提醒國人的研究�,亦不無些微意義?!?
誰都知道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的研究,應(yīng)注重于民間記錄的捜集�����。所以近代史家對于素為人所不道的商店帳簿�����、民間契約等都珍重地保存����、利用�����,供為研究的素材�。在外國且有許多的專門學(xué)者,埋首于此項(xiàng)資料的搜集和整理�,完成其名貴的著作,而在我國則方正開始萌芽����。本書對于此點(diǎn)也特加注意……這一個(gè)史料搜集法�,為推進(jìn)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���。
他所指的“近來一般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家”�,其意應(yīng)包涵年鑒學(xué)派及受其影響的史家��,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鑒學(xué)派��,而是根植于中國社會(huì)史論戰(zhàn)和農(nóng)村性質(zhì)論戰(zhàn)后的中國學(xué)術(shù)文化土壤�����,和吸收蘇聯(lián)和日本學(xué)術(shù)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���。本土的學(xué)術(shù)淵源���,則有章學(xué)誠的六經(jīng)皆史論、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��、胡適的歷史考證文章�����、顧頡剛的《古史辨
 吸收與互動(dòng):西方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學(xué)與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
吸收與互動(dòng):西方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史學(xué)與中國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派